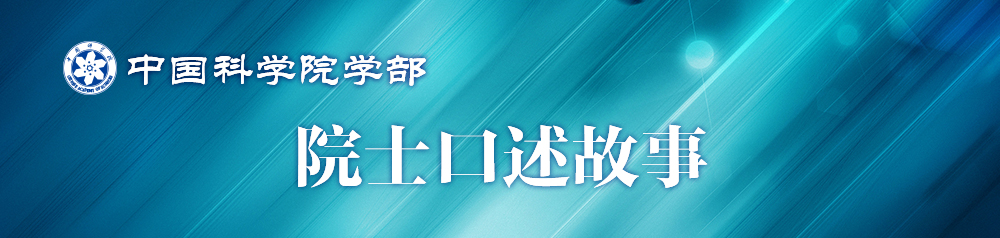涂光炽:开拓矿业、发展地学的一位先知先觉先行者——缅怀侯德封先生

侯德封(右一)在野外考察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今年正值侯德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文创作于2000年)。我有幸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在先生指导下参与了一些科研与管理工作。虽在其余时段与先生接触不多,但他治学为人的风范、高尚的品德与务实的作风,皆令我深受感动,获益良多。值此纪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谨就开拓矿产资源与发展地学两方面,谈谈个人与先生相处的体会与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先生便积极投身于普查找矿工作。1950年,他参与并领导了东北地区的矿产勘查。据曾与他共事的刘东生先生回忆,先生亲赴辽宁清原、吉林磐石一带实地考察,除运用传统的地质填图与剖面测量方法外,还引入新技术,在辽宁发现镍矿,在吉林找到白钨矿产地。此后,先生还主持了铁、锰等矿产的找矿工作。
1955年,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时任所长的侯先生主持全所科研事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亲自抓矿产资源的调查研究,提出问题、制定方案、调配力量,力求在科研上取得突破。
1956年夏,先生赴柴达木盆地参与并指导我所的石油地质工作。在野外,他反复强调以陆相生油理论与盆地分析为指导进行找油。同年,地质研究所在兰州设立研究室(即今兰州地质研究所前身),先生明确其任务:一是配合石油勘查,二是开展西北空白地区的前期地质调查。
1958年,在先生倡议下,我所提出建立十大稀有元素基地的设想。当时国内地学界对锂、铍、铌、钽、锆、铪、稀土等稀有元素仅知其关乎尖端技术,而对矿床类型、成矿机制、元素地球化学行为及找矿方法等知之甚少,甚至“稀有元素”一词尚属新鲜。美、苏及西欧的相关研究比我国早约二十年。在此背景下,提出对稀有元素成矿开展大规模摸底研究,实需胆识与魄力。我所随即组建若干调研小队,开展初步野外观察与分析测试。经努力,部分小队提交了较有分量的报告,如关于煤中锗、盐湖锂、白云鄂博与腊厂稀土等的研究。尽管受当时“左”的思潮干扰,基地的提法、要求与措施存在不足,对科研造成一定影响,但此项工作对我国稀有元素资源的开拓及相关地质地球化学研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侯老带领我们进入了这一近乎空白的领域。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响应国家“大力协同”号召,我所决定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铀矿地质研究。作为一项新任务,需先进行调研。在二机部同志陪同下,侯先生率领叶连俊先生、李璞先生与我,对湘粤、浙赣、河西走廊、川甘边境等地的花岗岩型、火山岩型、砂岩型及炭硅泥岩型铀矿进行了短期考察。先生在野外不仅作学术报告,更注重实地调查、听取意见,回所后即部署与相关部门的科研合作。
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我国矿床学与矿业新领域的开拓中,侯先生确实发挥了先知先觉与先行者的关键作用。

1956年,侯德封(正中)与叶连俊(左三)等中苏科学家在小兴安岭锰铁矿区考察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作为地质研究所的负责人,先生为我国固体地球科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常以远见卓识在关键时刻提出关键问题与对策。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区陆续开展小比例尺地质调查与填图。为配合并支持此项工作,先生提出我所应开展空白区路线地质调查,以获取地层、构造、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的轮廓性认识。这项快速大范围取得的成果,可为后续系统地质工作提供基础框架,是一项目标明确的先行任务。这一设想得到所有关研究室支持。经多次讨论,最终选定介于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之间的祁连山作为目标空白区。1956–1957年,我所联合古生物研究所、北京地质学院开展多学科综合调查,完成15条路线地质考察,初步划分了祁连山构造岩相带,确认走廊南山广泛出露早古生代火山岩,而柴达木北缘多见未变质的晚古生界。这些成果为祁连山的系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侯先生多次听取汇报并指导总结,还指示新成立的兰州分所也投入力量开展薄弱区研究。
先生很早就认识到第四纪研究的综合性、多学科性及其特殊意义,并注意到我国第四纪地质的独特性。在他的积极推动下,50年代前期我所即设立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由刘东生先生任主任。同时,依托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这一学术团体,并创办专业期刊。这些举措为我国第四纪多学科研究的早期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生同样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建设与人民生活中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的需求,于50年代中期设立相应研究室,由谷德振先生担任主任。
早在早期地质工作中,先生便萌发了元素地球化学思想,50年代初提出“化学地史”概念。随着对地球化学在固体地球科学中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他于1957年建议设立地球化学研究室,由司幼东先生任主任。1964年秋,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三线建设精神,决定在西北、西南建立学科中心,贵阳被选为化学中心所在地。先生提出,我所应支援三线建设,将部分研究室迁至贵阳,组建地球化学研究所,依托化学中心推动学科发展。这一倡议获全所响应并经中国科学院批准。1966年春,地球化学研究所于贵阳新实验大楼前正式挂牌,先生兼任首任所长。尽管“文革”干扰使化学中心未能实现,建所过程艰难,但全所同志仍坚持工作,为推动中国地球化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每念及此,无不感佩先生的远见与果决。
1958年,先生还推动建立同位素地质研究室,该室在重组后的序列中位列第一,称第一研究室。该室的成立、人员与主要设备(包括地质用质谱仪)的调配,以及李先生出任主任,均得益于先生的决策与努力。
“文革”前,先生已从医学界获悉东北地区克山病、大骨节病流行情况,认为地学也应参与地方病病因与防治研究。60年代后期,地球化学研究所组织力量承担地方病项目,后在此基础上成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室。
50年代的地质研究所建所不久,却不拘泥于传统地学机构格局,除发展地层、构造、沉积、矿物、岩石、矿床等传统学科外,还迅速开拓了第四纪地质、水文工程地质、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等新领域,设立相应研究室并加强人才与设备配置。这些新方向很快产出成果,在国内起到引领作用。至60年代初,我所已成为学科齐全、人才荟萃的地学重镇,从而为日后分出并组建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以及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等单位奠定了基础。毫不夸张地说,地质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固体地球科学的“母所”。这固然归功于院所两级正确领导与全所同仁努力,但先生的远见卓识、深思熟虑与善抓机遇,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时不禁想起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之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靠数学或实验技巧,而提出新问题、新可能性,从新角度审视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侯先生在地质研究所,不正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举措的引领者吗?
(节选自第四纪研究,2000,(01):6-8)